第六十二章 殖民扩张与战争(第2/3页)
全盛时期的雅典或佛罗伦萨,其人口也只不过是堪萨斯城的十分之一。可如果这两个地中海小城中只要一个不曾存在过,我们目前的文明就会是另外一种景象。密苏里河畔的繁华大都市堪萨斯城显然没有如此高的历史地位(我谨此向怀安特县的好人们致以诚挚的歉意)。
由于我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请允许我讲述另一个事实。
当我们准备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们必须事先弄明白他到底是外科医生、门诊医生、顺势疗法医生或者信仰疗法医生,因为我们要清楚他会从哪个角度来为我们治病。我们在为自己选择历史学家时,也该像选择医生那样谨慎。我们常常这样认为,“好呀,历史就是历史”,于是抓起一本历史书就乱读一气。可一个在苏格兰偏远落后、受严格长老会教派教养长大的作者,和一个从小就被领去听不相信任何魔鬼存在的罗伯特·英格索尔的精彩讲演的邻居,他们看待人类关系中的每一个问题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到了一定的时候,即使他们后来早就忘记了早期的教育,也不再踏足教堂或讲演厅,但是童年时代在他们身上烙下的早年的印象会一直跟随他们,在他们的言谈举止和写作中无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在本书的前言中,我曾告诉你们,我并不是没有错误的历史向导。现在本书将近尾声,我还是要重复这一点。我生长在一个老派的自由主义家庭,在这个对达尔文及其他19世纪科学先驱持宽容态度的环境中成长。我的童年生活几乎是和我的叔叔一起度过的,他收藏了16世纪伟大的法国散文作家蒙田的全部著作。因为我出生在鹿特丹,在高达市求学,不断接触到埃拉斯穆斯这位伟大的宽容者,出于某种自己也弄不清楚的原因,这位“宽容”的伟大倡导者征服了并不宽容的我。后来,我发现了阿尔托·法朗士(法国小说家),而我与英语的第一次接触是偶然看到一本萨克雷的《亨利·艾司芒德》。在所有的英文作品中,这部小说留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
如果我出生在一个舒适的中西部城市,也许会对童年听过的赞美诗情有独钟。可我对音乐的最早记忆,要追溯到童年的一个午后,我母亲第一次带我去听巴赫的赋格曲。这位伟大的清教徒音乐大师完美乐章征服了我纯洁的心灵,以致一旦我听到祈祷会上普通的赞美诗,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严厉的惩罚,令我苦不堪言。
如果我出生在意大利,从小就享受着阿尔诺山谷温暖和煦的阳光,那么我也会热爱绚丽夺目、光线明亮的图画。可我现在对这些之所以毫无感觉,那是因为我早期的艺术熏陶来自于一个天气阴沉的国度。那里少有阳光,天空灰蒙,极少会有雨过天晴的时候,偶尔投下的阳光猛烈照射着大地,使一切都呈现黑白分明的景色。
我特意举出这些事实,好让你们了解这本历史书的作者本人的倾向。这样也许你们能更好地理解他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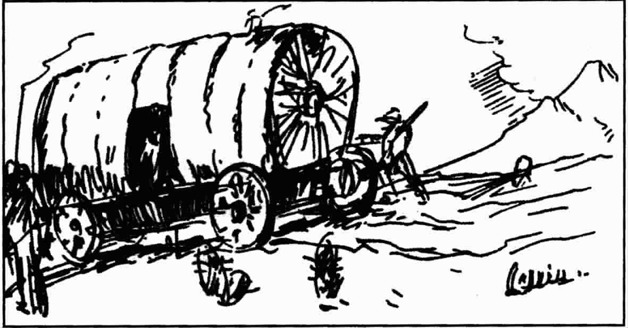
征服西部
说过这段简短但必要的题外话之后,让我们回到最近50年的历史上来吧。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事情,但似乎都不是那么至关重要。大多数强国不再仅仅是政治机构,他们还变成了大型商业企业,他们修筑铁路,他们开辟并资助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航线。他们发展电报事业,将自己与不同的属地联系起来。并且,他们稳步扩充着在各大陆的殖民地。每一块可能的亚、非领土都被这些敌对强国中的某一个所占有。法国宣布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安南(今越南)及东京湾(今北部湾)是他的领地。德国声称对西南及东部非洲的一些地区拥有所有权。他不仅在非洲西海岸的喀麦隆、新几内亚及许多太平洋岛屿上建立了定居点,还以几个传教士被杀作为冠冕堂皇的借口霸占了中国黄海边上的胶州湾。意大利人阴谋将阿比尼西亚(埃塞俄比亚)据为己有,结果被尼格斯(埃塞俄比亚国王)的黑人士兵打得惨败,只好从土耳其苏丹手里夺取了北非的的黎波里聊以自慰。俄国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又强占了中国的旅顺港。在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强占了台湾岛,1905年又宣布朝鲜国是他的殖民地。1883年,世界上空前强大的殖民帝国——英国,对埃及采取“保护”措施。他竭尽全力完成这项任务,并且掠取了这个被忽略的国家的物质财富。1886年苏伊士运河开通以后,埃及就一直处于外国侵略的威胁之中。英国卓有成效地实施着自己的“保护”计划,同时攫取巨大的物质利益。在接下来的30年时间里,英国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1902年,经过3年苦战,他征服了由德瓦士兰和奥林琪自由州组成的布尔共和国(即现在的南非)。与此同时,他还鼓励野心勃勃的殖民者塞西尔·罗兹为一个巨大的非洲联邦打下基础。这个国家从非洲南部的好望角一直延伸到尼罗河口,还一个不漏地把没有欧洲主子的岛屿和省份都纳入自己的囊中。